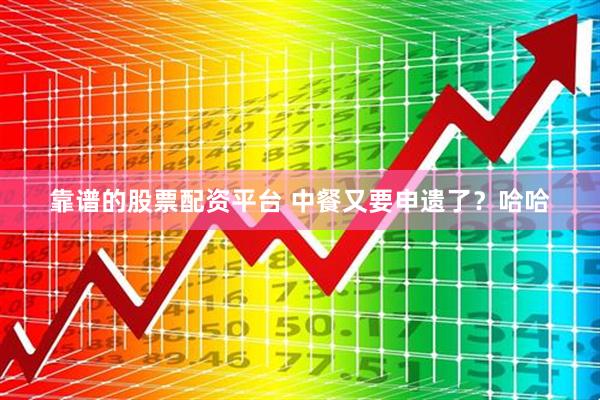

撰文 | 魏水华靠谱的股票配资平台
头图 | canva
继2011年和2015年中餐两次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(UNESCO)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》失败之后,2026年,中餐的第三次申遗已经被提上日程。
这次申遗的文本提报主题是:Chinese cuisine: knowledge and practic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regarding the preparation and enjoyment of food。
回顾前两次失败,2011年中餐申遗的申报主题是:“中国传统烹饪技艺”。
2015年中餐申遗的申报主题是:“中国菜”。
这次翻译过来则是——中国的烹饪和菜。
能申遗成功吗?哈哈哈哈哈哈。


前两次申遗,中国是怎么失败的?
2011年,信心满满的中国烹饪协会牵头开始中餐的第一次申遗。
协会专门成立了中餐申遗工作办公室,完成了包括顶层设计、专家论证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关、行业参与、大众支持、报告撰写、视频拍摄等一系列具体工作。
此外,协会还推动政府能尽早将中餐申遗提上国家战略日程,列入政府有关部门优先考虑的重点项目;另一方面则举办多项以中餐申遗为主题的“走出去”活动对中国美食文化进行海外推广。
以上文字,摘自中国烹饪协会的旧新闻。
最后摆在评审面前的,却是“满汉全席”的铺陈,文思豆腐的刀工,剁椒鱼扇的辣烈。看得人眼花缭乱。
最后失败的原因?
评审们不明白,这是厨师学校的教材,还是申遗文本。
事实证明,中国人从不缺越挫越勇的大无畏精神。
2015年,中餐二次申遗,选择了以广式烧鸭、剁椒蒸鱼、文思豆腐羹、梅干菜焖肉等几道代表性菜品,同样未能成功。
评审翻到最后,仍旧不明白:这是一本菜单?还是一本食谱?
时任中国烹饪协会会长姜俊贤总结说:“中餐背后的文化背景营造程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。”
然而什么是文化背景?
汉语里的文化这个词,概念远比英语词culture宽泛:乾隆皇帝吃过几次苏造肉可以是文化、淮扬菜大师切豆腐精细到毫米可以是文化、干菜焖肉里混合了几种干菜也可以是文化,但他们都不是culture。
拉丁文culture的原意是:灵魂的培养。
在中国,很多自以为懂得“美食文化”的人,理解错了。

2013年,日本的“和食”申遗成功。
很多人惊讶:凭什么?我们菜比他们多啊!
但日本提交的,不是寿司拼盘、不是天妇罗、也不是寿喜烧,而是一种“文化体系”。
在申遗文本里,他们写的是:
自然观:饮食体现“山川海物”的四季更替,人与自然的和谐。
节令感:饭桌与正月、盂兰盆节、红叶季紧密相连。
社会秩序:和食是家庭餐桌的日常方式,体现代际传承与秩序。
健康与可持续:清淡、少油、注重原味,被视为一种责任。
在京都的老宅子里,祖母按照节气煮汤:春分用樱花形的面饼,立冬放萝卜与小鱼干。孩子喝下去的,不只是味道,而是时间的节律。
这就是餐桌上的普世价值。
和食成功的关键,是它把“吃”解释为一种“生活方式”。寿司、味噌汤只是符号,真正的价值是“人与自然如何相处”“社会如何通过饮食延续”。
2020年,日本的“清酒”也被列入非遗。
这一次,世界看见的不是酒精浓度,不是酿造工艺,而是文化的脉络:
清酒是神道祭祀不可或缺的供品。
是乡村共同体的分享纽带。
是年节仪式里象征丰收与团圆的媒介。
在新潟的神社,新米收割后要先酿清酒,供奉给神明;在正月,村民聚在一起开坛,老人分酒,小孩啜饮,酒杯传递的是一种“共同体”的归属感。
清酒不是酒,而是稻米—水源—神社—节日—家庭的一整套生态。
日本提交的和食、清酒申遗文本,没有喊“博大精深”,没有说“历史五千年”。只是冷静地写:这是我们的日常,我们从中获得身份认同。
这份克制,反而最有力。

更在中国餐饮行业心口来上一刀的,是韩国泡菜的申遗成功。
泡菜好吃吗?
对很多人来说好吃,但论及普世价值、论及全球范围内的接受程度,也就这样。哪怕在中国,在很多正式的宴饮场合,它也是个不怎么能上台面的东西。
泡菜难做吗?
四个字概括“没有门槛”,在中国、越南、日本、外蒙古,都有各自的泡菜,它不需要复杂的工序、也不需要精准的技术。
但韩国申遗的不是泡菜本身,而是“腌制越冬泡菜文化”
在中国的《诗经》里,出现了“菹”字,它在中国的字典里被解释为酸菜,它广泛流行于中国的江浙、四川、闽粤和东北。
但在申遗文本里,韩国人则刻意回避了泡菜腌制的技术和流派。强化了代代相传的越冬泡菜,反映了邻里间“分享”的精神,增强了人们之间的纽带感和归属感,还专门为泡菜设立了国家节日。
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的是什么,其实底层逻辑很简单。

2003年,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》写得清清楚楚:
遗产,是代代相传的实践、表现、技艺和知识体系;是社区与群体认为属于自身文化的部分;是承载身份与认同的纽带。
换句话说,遗产不是盘里的“菜”,而是桌边的“人”。不是烹饪的“技艺”,而是饮食的“方式”。
然而,中国的申遗逻辑,总绕不过一个思维定势:把“烹饪技艺”当成“饮食文化”。
于是我们申遗时,摆上去的是刀工十八般、火候千层次,讲的是满汉全席的山珍海味。可评审看到的,只是一场盛宴的陈列。它像博物馆里的展品,可以惊叹,却没有生命。
一块豆腐被切成上百丝,漂在清汤里,固然让人佩服,但这能说明什么?能说明中国人如何在节日里守护家庭?能说明我们如何在四季中与自然共生?
真正的culture,常常在极寻常处。
《荆楚岁时记》里写春社日的食俗:“四邻共醵钱买酒肉,祭社毕,聚饮,谓之打社。”
邻里们凑钱买酒肉,一起祭祀,一起喝酒。隐喻开春之初,物产贫乏之时互相搀扶,共度难关的古老传统。
《东京梦华录》里写的开封市井的食俗:“人家新婚,必蒸馒头大如斗,以祈多子。”
一整块白面团,蒸出来像小山。婚礼过后,把大馒头分给邻里,象征家族繁衍、福泽共享。
这才是“饮食文化”的真实模样——通过一口食物,确认共同体的存在。
遗产要回答的问题,是“为什么”,而不是“多么精致”。
然而,是什么时候开始,我们把文化叙事,让位于技艺的堆叠?

今天的中餐行业,是个什么样的江湖呢?
厨房里,徒弟拜师是需要磕头的。
敬茶、叩拜、送上谢师礼。
师傅趾高气扬,安心领受,摆出媳妇熬成婆的姿态。
在当代餐饮高度专业化、全球化与知识透明化的背景下,传统中餐厨房所依赖的“师徒制”,实际上是一种结构性的落后与文化惰性。
尤其当厨师职业教育体系日趋完善、烹饪技术门槛被系统化教学大幅拉平、全球食材与技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通时,中餐圈内仍顽固保留的“拜师磕头”“秘方私授”“江湖帮派”等旧习,不仅无益于技艺传承,反而成为阻碍行业进步的桎梏。
传统中餐师徒关系,本质上是一种以人身依附为基础的交换契约:
徒弟通过长期无偿或低偿劳动,端茶倒水、洗衣做饭、随叫随到,换取师傅“口传心授”的所谓“秘方”或“绝活”。这种模式在信息闭塞、技术垄断的时代有其生存土壤,但在今天,一道“秘制酱汁”的成分早已可通过质谱仪分析,一个“火候秘诀”也能在烹饪科学课程中被解构为温度与时间的函数。所谓“秘籍”,更多是经验模糊性的遮羞布,而非不可复制的核心技术。
所以,中餐厨房里的师徒关系,已经异化为权力寻租——师傅以“传承人”自居,实则将厨房变为私人领地,利用徒弟的忠诚构建小圈子,排斥“非我门徒”的同行,形成封闭的利益集团。这种“江湖气”不仅扼杀创新,更滋生职场霸凌与资源垄断,让真正有才华但无“门路”的年轻厨师难以出头。
反观西餐厨房体系,虽也存在等级,但其核心是“专业分工”与“能力导向”。主厨(Chef)的权威建立在技术实力、管理能力与菜品创造力之上,而非血缘或拜师仪式。西餐教育虽有学院派基础,但真正的厨艺精进发生在后厨实战中。
而这一“实战缺口”,恰恰由主厨制有效弥补:新人从Commis(帮厨)做起,在清晰的岗位职责与标准化流程中积累经验,晋升路径透明,能力决定位置。
主厨的角色不是“宗师”,而是技术领导者与团队教练,其价值在于整合资源、激发创意、确保出品,而非垄断“秘方”。更重要的是,西厨文化强调开放交流——厨师流动频繁,食谱共享普遍,国际赛事与媒体平台鼓励技艺展示,这使得整个行业处于动态进化中。
当然,西厨体系并非完美,其高压与标准化也可能压抑个性。但它建立在现代职业伦理之上:尊重专业、承认个体价值、鼓励知识流动。而中餐师徒制若继续沉溺于磕头拜师、秘方护短、门派之争的旧梦,只会让整个行业在内耗中落后。
真正的传承,不是跪着接过的“秘籍”,而是在开放、平等、专业的环境中,让每一代厨师都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,看得更远,做得更好。在技术民主化的时代,厨房不需要“江湖”,只需要专业与尊重。
而这,也正是中餐申遗屡战屡败的症结所在。

当然,文化脱钩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。
你可以说,让日韩积极融入西方叙事,申他们的世界遗产;中国菜的博大精深、刀工火候,中国人自己享受便是。
但现实是,2026年中餐第三次申遗已成定局,中国已经提交了新的文本。
餐饮协会喊口号:“这一次,一定要成功!”
文化部门喊口号:“中餐是世界的宝藏!”
可目前透露出来的内容,却依旧熟悉:强调“博大精深”“八大菜系”“刀工火候”。
依旧是技艺的炫耀,而不是文化的叙事。
评审要看的是:中餐如何塑造身份?如何维系家庭?如何回应自然?
而我们的文本,却可能继续写:
“剁椒蒸鱼扇,色香味俱全。”
这就是错位。
烹饪界以为“技艺就是文化”,文化界以为“历史就是价值”。两边错位,结果就是:再失败一次。
所以,2026年,能不能?
哈哈


长富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